這位已經(jīng)70歲的企業(yè)家,親手創(chuàng)辦了福耀集團(tuán),從做水表玻璃起家,到2013年成為中國(guó)第二、全球第二的玻璃大王。
有人說(shuō)曹德旺身上很矛盾:辦公室大得像籃球場(chǎng),午餐卻只在公司食堂草草解決,不超過(guò)5分鐘;在福州蓋了6000平米豪宅,卻將手中70%的公司股份捐給了慈善基金會(huì);作為一名集團(tuán)董事長(zhǎng)和佛教徒,又坦然承認(rèn)自己曾經(jīng)在婚姻中碰到的問(wèn)題。
真實(shí),或許是對(duì)曹德旺最為貼切的描述。相比中國(guó)新一代企業(yè)家,老一輩的企業(yè)家們往往給人“悶聲發(fā)大財(cái)”的低調(diào)印象,這也是中國(guó)人的一大處世哲學(xué)。
成年人的真實(shí)背后往往是勇氣。與“皇帝的新衣”故事中那名說(shuō)真話的小男孩不同的是,在商界奮戰(zhàn)了半生了曹德旺,并不是一名無(wú)知者。在曹德旺“要考慮如何提高國(guó)家競(jìng)爭(zhēng)力的問(wèn)題,不要整天拍馬屁、不著邊際的胡說(shuō)八道”言論的背后,是他坦然說(shuō)真話的勇氣。
在他的自傳中,他大談自己在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倒買倒賣的發(fā)家史、與地方政府的斗爭(zhēng)史以及創(chuàng)業(yè)過(guò)程中對(duì)一些合作伙伴的不滿。
如今,他的坦然與勇氣,引發(fā)了關(guān)于中國(guó)制造業(yè)成本難題的大討論。曹德旺的“真話”,道出了中國(guó)制造業(yè)的困境。中國(guó)經(jīng)濟(jì)下行大背景下,稅負(fù)、原料價(jià)格、環(huán)保嚴(yán)令等多重因素讓制造業(yè)面臨著比過(guò)去更難得境地,而曹德旺的話,一下子把這些問(wèn)題鋪開擺在了公眾眼前。
實(shí)業(yè)之難
玻璃大王、全球第二、中國(guó)首善……福耀集團(tuán)董事長(zhǎng)曹德旺身上不乏這類光環(huán)與標(biāo)簽。
但他因?yàn)橐环P(guān)于中、美制造業(yè)成本對(duì)比的言論而獲得另一種關(guān)注。“中國(guó)制造業(yè)的綜合稅負(fù)比美國(guó)高35%,土地基本不要錢,電價(jià)是中國(guó)的一半,天然氣價(jià)格是中國(guó)的四分之一,中國(guó)較美國(guó)有優(yōu)勢(shì)的,只有勞動(dòng)力。”曹德旺在采訪中口無(wú)遮攔的表達(dá)被輿論冠以“曹德旺跑了”的標(biāo)題給“帶歪了”。
這與曹德旺發(fā)表此番言論的初衷相去甚遠(yuǎn),畢竟福耀集團(tuán)有三分之二的業(yè)務(wù)都來(lái)自中國(guó),正如曹德旺自己所稱,他沒(méi)跑,他的事業(yè)重心在中國(guó)。
16歲開始經(jīng)商的曹德旺,對(duì)企業(yè)的成本與風(fēng)險(xiǎn)有著異于常人的敏銳。2006年,正值金融危機(jī)來(lái)臨前夕,人民幣匯率略有浮動(dòng),勞保法、環(huán)保法、公路法隨后相繼出臺(tái),從這些蛛絲馬跡中,曹德旺嗅到了危險(xiǎn)的氣息。
他的判斷是,人民幣升值、各項(xiàng)法律法規(guī)的實(shí)施,將給以出口為主業(yè)的中小微制造業(yè)帶來(lái)無(wú)法承受的成本。而有廣東增城市的地方干部告訴曹德旺,幾乎每天都有企業(yè)蒸發(fā)、老板跑路。2007年4月,他曹德旺判斷危機(jī)將在三年內(nèi)發(fā)生,集團(tuán)必須抓緊將生產(chǎn)、管理、營(yíng)銷成本都降下來(lái),并隨后關(guān)閉了4條建筑級(jí)浮法線。
2008年,曹德旺預(yù)判的金融危機(jī)如期而至,福耀集團(tuán)提前準(zhǔn)備的自救行動(dòng)起到了作用,并且還有余力支援其他下游汽車企業(yè)。
當(dāng)時(shí),為了應(yīng)對(duì)金融危機(jī),中國(guó)政府加大了政策拉動(dòng)力度,鋼鐵、水泥、玻璃等制造業(yè)迎來(lái)進(jìn)一步需求增長(zhǎng),國(guó)家GDP增長(zhǎng)率仍保持高速。而如今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下行壓力加大,制造業(yè)迎來(lái)陣痛。
去年,波士頓咨詢發(fā)布的一份報(bào)告顯示,受人力成本、匯率和能源成本等因素影響,中國(guó)制造業(yè)的綜合成本已經(jīng)只比美國(guó)低5%。而剛剛贏得美國(guó)總統(tǒng)大選的特朗普則聲稱,要讓制造業(yè)重回美國(guó),“中國(guó)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搶走了金錢……我們要把工作拿回來(lái)”。
從“別讓華為跑了”到“曹德旺跑了”,這些調(diào)侃式傳聞其實(shí)更多揭示了中國(guó)制造業(yè)面臨的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中國(guó)宏觀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中國(guó)的制造業(yè)對(duì)成本的波動(dòng)越來(lái)越敏感。而曹德旺的一番言論,將這些現(xiàn)實(shí)一件件擺在了大家的眼前。
關(guān)于中美制造業(yè)的對(duì)比并非新話題。2014年,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纖有限公司(下稱“江南化纖”)的一份關(guān)于中美制造業(yè)成本對(duì)比的數(shù)據(jù),得出了與曹德旺類似的結(jié)論,并廣泛流傳。
2014年,江南化纖公司在美國(guó)南卡羅萊納州投資辦廠,成為首家在美國(guó)建立再生聚酯短纖維制造工廠的中國(guó)企業(yè),一期計(jì)劃投資2500萬(wàn)美元,二期計(jì)劃投資2000萬(wàn)美元。
在江南化纖關(guān)于中、美創(chuàng)辦同等規(guī)模企業(yè)的成本對(duì)比中,在土地、物流、銀行借款和能源成本上,中國(guó)的成本分別是美國(guó)的9倍、2倍、2.4倍和2倍以上。這樣的差距同樣引起了外界的關(guān)注。“這樣簡(jiǎn)單的成本對(duì)比是較為片面的。”江南化纖辦公室工作人員說(shuō),中美的成本對(duì)比是客觀存在的,只是沒(méi)有結(jié)合企業(yè)的銷售、市場(chǎng)實(shí)際情況。這位工作人員還告訴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對(duì)于類似福耀集團(tuán)和江南化纖這樣有進(jìn)出口業(yè)務(wù)的企業(yè)而言的,還要面臨人民幣匯率波動(dòng)的問(wèn)題。“企業(yè)都是逐利的,哪里有利潤(rùn)就到哪里建廠,這是很正常的事,那么多外企也到中國(guó)來(lái)建廠,這不是合理的嗎?”上述江南化纖工作人員告訴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記者,合理的對(duì)比應(yīng)該是計(jì)算一個(gè)產(chǎn)品最終在美國(guó)銷售為前提,在中國(guó)制造并出口到美國(guó)和在美國(guó)本土制造的各自成本分別是多少,這樣以市場(chǎng)、銷售為導(dǎo)向的成本測(cè)算,才是合理的。曹德旺近日也發(fā)表了類似的言論。近日在接受《環(huán)球時(shí)報(bào)》采訪時(shí),曹德旺稱,美國(guó)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chǎn)國(guó),福耀作為汽車玻璃的制造商,當(dāng)然要在美國(guó)設(shè)廠,打進(jìn)美國(guó)市場(chǎng),并稱福耀只是中國(guó)企業(yè)對(duì)外投資步伐加大的一個(gè)縮影,今年以來(lái),中國(guó)的對(duì)外投資規(guī)模超過(guò)實(shí)際利用外資趨勢(shì)愈加明顯,中國(guó)對(duì)外投資已實(shí)現(xiàn)13年連續(xù)增長(zhǎng),年均增幅高達(dá)33.6%。
而福耀玻璃在2010年財(cái)報(bào)中便透露出一種危機(jī)意識(shí),首次透露了圍繞企業(yè)的一系列風(fēng)險(xiǎn),包括成本攀升、市場(chǎng)變數(shù)以及匯率上浮一系列不可控因素,步步逼近企業(yè)。根據(jù)其財(cái)報(bào)中表述,2010年10月起,CPI已連續(xù)四個(gè)月漲幅超過(guò)4%,兩個(gè)月內(nèi)中央政府多次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宏觀經(jīng)濟(jì)的積極調(diào)控。公司產(chǎn)品主用原料如浮法玻璃、PVB原料等,正受天然氣定價(jià)、原油、煤電等改革機(jī)制作用下,價(jià)格步步攀升,加劇成本問(wèn)題。
更大的威脅,在于汽車市場(chǎng)的一系列變數(shù)。在那兩年,北京“限購(gòu)令”正逐步引起其他城市效仿。公司在財(cái)報(bào)中描述了國(guó)內(nèi)汽車產(chǎn)量,在2009年到2010年經(jīng)歷連續(xù)30%以上的爆發(fā)式增長(zhǎng)后,中國(guó)成為了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chǎng)。發(fā)展至頂端的汽車市場(chǎng),似乎意味著市場(chǎng)增速放緩。2011年1月汽車產(chǎn)量環(huán)比下降3.58%,僅同比增長(zhǎng)11.33%。作為一家專注生產(chǎn)汽車玻璃,重度依賴汽車行業(yè)的公司,福耀需要在國(guó)際上進(jìn)一步開拓市場(chǎng)。
海外之路
曹德旺出海的決心,源于1996年與法國(guó)圣戈班一次失敗的合作。圣戈班是一家專注于建筑、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和工業(yè)應(yīng)用等方面材料研發(fā)、制造與銷售的國(guó)際化公司。1996年,曹德旺和圣戈班達(dá)成協(xié)議,圣戈班入股福耀集團(tuán),持有42%股份,成為控股股東,曹德旺繼續(xù)擔(dān)任福耀集團(tuán)董事長(zhǎng)。
曹德旺的想法是通過(guò)圣戈班先進(jìn)的技術(shù),能夠幫助福耀集團(tuán)進(jìn)行國(guó)際化,進(jìn)軍海外市場(chǎng)。然而,圣戈班是一家國(guó)際化的集團(tuán),對(duì)其全球各地的子公司都有分工,它對(duì)福耀的定位卻僅僅是服務(wù)好中國(guó)的市場(chǎng)。
圣戈班與福耀3年的合作時(shí)間里,曹德旺向圣戈班傳達(dá)的中文、英文、法文報(bào)告摞起來(lái)有50厘米高,卻沒(méi)有一份獲得批準(zhǔn),曹德旺甚至都不知道法國(guó)方面是誰(shuí)在負(fù)責(zé)管理。
曹德旺明白,圣戈班這是在逼他下野。最終,在1999年福耀集團(tuán)與曹德旺聯(lián)手,出資3000萬(wàn)美元回購(gòu)了圣戈班的股份,徹底脫離了圣戈班。也正是此番經(jīng)歷讓曹德旺明白以前自己崇拜的五體投地的500強(qiáng)公司不過(guò)如此,這堅(jiān)定了曹德旺走向國(guó)際化的決心。
如今,這家汽車玻璃制造巨頭超過(guò)三成的營(yíng)業(yè)收入來(lái)源國(guó)外,據(jù)其官網(wǎng)資料,福耀的產(chǎn)品占全球市場(chǎng)份額20%,2013年,其以營(yíng)業(yè)收入115億元、凈利潤(rùn)19億元成為中國(guó)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制造商。
而對(duì)于海外業(yè)務(wù)超過(guò)三分之一的福耀而言,如何進(jìn)行全球化的資源配置,是國(guó)際化過(guò)程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正如“代工之王”臺(tái)灣鴻海(富士康)那樣,往低成本的地方去以獲得利潤(rùn),是企業(yè)與生俱來(lái)的逐利性。
今年10月,福耀在美國(guó)投資6億美元的代頓工廠舉辦了竣工儀式,曹德旺當(dāng)時(shí)說(shuō)未來(lái)福耀在美國(guó)的整體投資將達(dá)到10億美元,提供5000個(gè)就業(yè)崗位,是中國(guó)制造業(yè)對(duì)美最大投資之一。
“曹德旺跑了”——這是外界對(duì)福耀在美國(guó)投資設(shè)廠、曹德旺對(duì)比中、美制造業(yè)成本言論公開后的反應(yīng)。這延續(xù)了此前外界對(duì)“李嘉誠(chéng)跑了”的邏輯——近年來(lái)“首富”李嘉誠(chéng)在中國(guó)大量拋售資產(chǎn),并在英國(guó)進(jìn)行投資。
這并非是曹德旺第一次被外界傳聞“跑了”。1991年,當(dāng)時(shí)的福耀集團(tuán)謀劃上市之時(shí),外界曾流傳著曹德旺想圈錢跑到國(guó)外去的流言。流言自然是假的,曹德旺也沒(méi)有跑路。而這一次,曹德旺也向外界回應(yīng),自己已經(jīng)70歲,不會(huì)開車不會(huì)講外語(yǔ),進(jìn)不了主流社會(huì),去美國(guó)干什么?
真實(shí)的曹德旺
曹德旺與汽車玻璃結(jié)緣始于1984年。當(dāng)時(shí)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順便給母親買了一根拐杖,上車時(shí)司機(jī)提醒他,不要碰壞了玻璃不然“可賠不起”。“自己就是做玻璃的,怎么會(huì)賠不起?”曹德旺當(dāng)時(shí)愣了。后來(lái)一問(wèn),才知道汽車玻璃價(jià)格驚人,一款馬自達(dá)的汽車玻璃要六千元,若告急還要八千元,汽車玻璃如果破了,換起來(lái)很麻煩,因?yàn)闆](méi)有國(guó)產(chǎn)剝離,而進(jìn)口玻璃很貴。
曹德旺當(dāng)時(shí)想,如果自己生產(chǎn)的汽車玻璃賣個(gè)幾百塊,不僅替代了進(jìn)口的汽車玻璃,還能讓老百姓享受到實(shí)惠,自己又賺到了錢。
曹德旺很快便從費(fèi)功夫從各地購(gòu)買了汽車玻璃的圖紙、儀器設(shè)備并找來(lái)了技術(shù)人員,在1984年5月開始投產(chǎn)汽車玻璃。1987年,在福清縣政府的支持下,原專注于生產(chǎn)水表玻璃的高山玻璃廠改為縣里的合資企業(yè),專業(yè)生產(chǎn)汽車玻璃生產(chǎn)。1989年,中國(guó)汽車工業(yè)總公司參股。1993年,股票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成為中國(guó)同行業(yè)首家上市公司。
企業(yè)做大的過(guò)程中,企業(yè)多次與各方面利益群體發(fā)生沖突。1986年,全國(guó)開展農(nóng)村整黨整風(fēng)運(yùn)動(dòng),鎮(zhèn)黨辦主任來(lái)查玻璃廠的賬,隨后指控曹德旺貪污十萬(wàn)多元。曹德旺急了,找到從未見過(guò)的縣委書記,據(jù)理力爭(zhēng),盡管得到了書記的支持,但政黨辦隨后又將狀搞到了福清市和福建省農(nóng)委。
其實(shí),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就在省農(nóng)委辦公室工作,告狀曹德旺的信件都經(jīng)他手,但他沒(méi)有吭一聲,任由省里調(diào)查,最終證明了曹德旺的清白。而此后,1988年福建國(guó)際龍舟節(jié)面對(duì)省體委的違約、面對(duì)地方官方推來(lái)的人情工程,以及面對(duì)美國(guó)的傾銷指控,曹德旺總是按正面交鋒。
曹德旺經(jīng)商業(yè)半生,曾稱,自己這么多年最驕傲的事就是沒(méi)給官員送過(guò)一塊月餅。許多企業(yè)家出于各種需要或原因,參加各種頒獎(jiǎng)、典禮、俱樂(lè)部,發(fā)表高調(diào)口號(hào)、言論等,而曹德旺也很少出現(xiàn)在這類公開場(chǎng)合。
曹德旺說(shuō)自己不會(huì)跑,因?yàn)?ldquo;中國(guó)是中國(guó)人的中國(guó)”,企業(yè)家要有“報(bào)國(guó)為民的心態(tài)”。而曹德旺對(duì)“報(bào)國(guó)為民的心態(tài)”的心態(tài),就是金融、IT、房地產(chǎn)等行業(yè),賺錢再多也不做,理由是對(duì)國(guó)家沒(méi)有好處,許多人找他做私募基金,他卻寧可捐給慈善機(jī)構(gòu),并且最近還稱“中國(guó)制造業(yè)雖然很龐大,但還沒(méi)有進(jìn)入真正的工業(yè)化,卻已有進(jìn)入虛擬經(jīng)濟(jì)的趨勢(shì)”。
這都表明了曹德旺對(duì)玻璃和制造業(yè)的堅(jiān)守,以及他個(gè)人對(duì)實(shí)業(yè)的價(jià)值認(rèn)同。無(wú)獨(dú)有偶,同樣被認(rèn)為是中國(guó)制造業(yè)代表人物之一的格力電器董事長(zhǎng)董明珠,近日亦稱,90后不愿去實(shí)體經(jīng)濟(jì)工作,在家開個(gè)網(wǎng)店就能賺錢,對(duì)國(guó)家實(shí)體經(jīng)濟(jì)有隱患。
如今,贏得美國(guó)大選的特朗普計(jì)劃重振工業(yè),扭轉(zhuǎn)過(guò)去“去工業(yè)化”的進(jìn)程。而在中國(guó),盡管“中國(guó)制造2025”帶來(lái)的相關(guān)利好政策讓一些產(chǎn)業(yè)得到刺激,但像曹德旺這樣反映制造所面臨的真實(shí)困境的聲音,恐怕還會(huì)更多,也需要更多。
經(jīng)觀說(shuō)
一番關(guān)于中美制造業(yè)的成本對(duì)比,或許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商業(yè)實(shí)際,但反映了中國(guó)制造業(yè)的當(dāng)下困境。曹德旺掀起了社會(huì)對(duì)中國(guó)制造業(yè)的關(guān)注與討論,而中國(guó)作為制造大國(guó)也需要更多來(lái)自一線企業(yè)家真實(shí)的聲音。


 手機(jī)資訊
手機(jī)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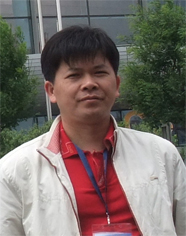


 豫公網(wǎng)安備41019702003646號(hào)
豫公網(wǎng)安備41019702003646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