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guān)于此輪經(jīng)濟(jì)下行的原因及其政策應(yīng)對(duì)在宏觀經(jīng)濟(jì)研究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廣泛的討論,大致分化為兩種認(rèn)識(shí):第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經(jīng)濟(jì)下行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出路在于刺激,“需求側(cè)總量刺激”;第二種觀點(diǎn)認(rèn)為經(jīng)濟(jì)下行是結(jié)構(gòu)性和體制性減速,出路在于改革,“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
無論從宏觀、中觀還是微觀,可以廣泛地觀察到,中國(guó)此輪經(jīng)濟(jì)減速主要是結(jié)構(gòu)性和體制性。更為重要的是,市場(chǎng)本該結(jié)構(gòu)性出清,卻由于體制性障礙難以實(shí)現(xiàn),刺激多、改革少,舊增長(zhǎng)模式拒絕退出,隱性擔(dān)保泛濫導(dǎo)致資金錯(cuò)配,形成三大資金黑洞(即舊增長(zhǎng)模式的鐵三角:房地產(chǎn)、地方融資平臺(tái)和產(chǎn)能過剩重化工業(yè)),醞釀金融風(fēng)險(xiǎn)和隱性失業(yè)。
政策應(yīng)對(duì)應(yīng)主要是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而非需求側(cè)總量刺激。如果經(jīng)濟(jì)減速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增長(zhǎng)平臺(tái)和動(dòng)力結(jié)構(gòu)不變,應(yīng)通過反周期性寬松政策刺激經(jīng)濟(jì)回歸增長(zhǎng)中樞。但是,如果經(jīng)濟(jì)減速是結(jié)構(gòu)性和體制性,增長(zhǎng)平臺(tái)和動(dòng)力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體制性因素阻礙了結(jié)構(gòu)性出清,固化了原有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產(chǎn)能過剩企業(yè)淪為“僵尸企業(yè)”,只刺激不改革實(shí)際上是延緩舊增長(zhǎng)模式出清和鼓勵(lì)加杠桿,是“明斯基時(shí)刻”并引向金融危機(jī)的節(jié)奏。
2008年國(guó)際金融危機(jī)以來,面臨經(jīng)濟(jì)下行,我國(guó)先后采取了以財(cái)政刺激、貨幣放水等為主的政策工具應(yīng)對(duì),但均未能有效解決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問題,并留下大量風(fēng)險(xiǎn)和后遺癥,政策取向最終選擇以“供給側(cè)改革”為主。
資本市場(chǎng)在供給側(cè)改革中將承擔(dān)重要使命。未來隨著A股逐步調(diào)整到位、泡沫去化進(jìn)入尾聲,推動(dòng)資本市場(chǎng)改革迎來重要機(jī)遇和時(shí)間窗口。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chǔ)制度扎實(shí)、市場(chǎng)監(jiān)管有效、投資者權(quán)益得到充分保護(hù)的股票市場(chǎng),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升級(jí)。大力推進(jìn)資產(chǎn)證券化,化解金融風(fēng)險(xiǎn)。發(fā)展開放、包容的多層次資本市場(chǎng),降低企業(yè)融資成本。鼓勵(lì)通過資本市場(chǎng)優(yōu)化重組,化解落后產(chǎn)能。依托資本市場(chǎng),放寬準(zhǔn)入,引入新的投資者,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yè)改革。實(shí)施結(jié)構(gòu)性減稅,鼓勵(lì)創(chuàng)新。推動(dòng)國(guó)企改革,提高資產(chǎn)證券化率。在推動(dòng)供給側(cè)改革的同時(shí),建設(shè)社會(huì)“完全網(wǎng)”,兜住社會(huì)穩(wěn)定的底線。
隨著供給側(cè)改革破冰攻堅(jiān),各界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前景將更有信心。
正文:
黨中央國(guó)務(wù)院十分重視發(fā)揮多層次資本市場(chǎng)在供給側(cè)改革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中的重要作用和使命。2015年中央經(jīng)濟(jì)工作會(huì)議提出“著力加強(qiáng)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并多次論述多層次資本市場(chǎng)在“去產(chǎn)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bǔ)短板”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12月23日國(guó)務(wù)院常務(wù)會(huì)議,“確定進(jìn)一步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措施,提升金融服務(wù)實(shí)體經(jīng)濟(jì)效率”。
一、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和需求側(cè)總量刺激:近年來我國(guó)經(jīng)濟(jì)面臨的問題、討論與政策應(yīng)對(duì)
經(jīng)濟(jì)分為供求,需求主要是指消費(fèi)、投資、出口和庫存,供給主要指資本、勞動(dòng)、技術(shù)和制度。經(jīng)濟(jì)問題分為需求問題和供給問題,如果經(jīng)濟(jì)下行主要是需求側(cè)總量問題,則應(yīng)該采取財(cái)政貨幣等需求管理工具刺激總需求;如果經(jīng)濟(jì)下行主要是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問題,則應(yīng)該通過改革破舊立新。與“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相對(duì)應(yīng)的是“需求側(cè)總量刺激”。
1、中國(guó)此輪經(jīng)濟(jì)下行主要是結(jié)構(gòu)性和體制性的,而非外部性和周期性的
近年來,關(guān)于此輪經(jīng)濟(jì)下行的原因及其政策應(yīng)對(duì)在宏觀經(jīng)濟(jì)研究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廣泛討論,大致分化為兩種認(rèn)識(shí):第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經(jīng)濟(jì)下行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出路在于刺激;第二種觀點(diǎn)認(rèn)為經(jīng)濟(jì)下行是結(jié)構(gòu)性和體制性減速,出路在于改革。
第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此輪經(jīng)濟(jì)下行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機(jī)以來的全球經(jīng)濟(jì)衰退,以及國(guó)內(nèi)周期性調(diào)整所致。如果未來全球經(jīng)濟(jì)復(fù)蘇,國(guó)內(nèi)周期性出清調(diào)整結(jié)束,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將周期性復(fù)蘇且還能重回8%-10%高增長(zhǎng)軌道。持外部性和周期性論者認(rèn)為,當(dāng)前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平臺(tái)和動(dòng)力結(jié)構(gòu)沒有發(fā)生變化,只是由于2002-2007年高速增長(zhǎng)堆積了大量低效產(chǎn)能、全球經(jīng)濟(jì)危機(jī)、等原因,導(dǎo)致了產(chǎn)能過剩和金融過度杠桿,隨后的去產(chǎn)能和去杠桿行為引發(fā)了經(jīng)濟(jì)減速。
但是,2013年以來世界經(jīng)濟(jì)持續(xù)緩慢復(fù)蘇,美國(guó)步入穩(wěn)固復(fù)蘇軌道并于2015年12月首次加息,歐日經(jīng)濟(jì)也筑底改善,但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速繼續(xù)放緩 。
第二種觀點(diǎn)認(rèn)為,此輪經(jīng)濟(jì)下行的主要原因是支撐原先高增長(zhǎng)的動(dòng)力結(jié)構(gòu)發(fā)生變化,導(dǎo)致經(jīng)濟(jì)潛在增長(zhǎng)率下降。2003、2008年劉易斯第一、二個(gè)拐點(diǎn)先后出現(xiàn),2012年15-59歲勞動(dòng)年齡人口開始出現(xiàn)凈減少,勞動(dòng)力成本持續(xù)大幅上漲,跨國(guó)公司轉(zhuǎn)移低端生產(chǎn)基地,加工貿(mào)易告別高增長(zhǎng)時(shí)代,低端加工制造業(yè)領(lǐng)域普現(xiàn)產(chǎn)能過剩;2014年20-50歲置業(yè)人群達(dá)到峰值并開始減少,城鎮(zhèn)戶均達(dá)到一套,城鎮(zhèn)化率達(dá)到54.77%,房地產(chǎn)長(zhǎng)周期拐點(diǎn)出現(xiàn),三四線城市面臨去庫存壓力,房地產(chǎn)開發(fā)投資增速從2014年初的19.3%下滑到2015年1-11月的1.3%;居民從住行消費(fèi)向服務(wù)消費(fèi)升級(jí),重化工業(yè)產(chǎn)能過剩加劇;國(guó)內(nèi)產(chǎn)能過剩疊加國(guó)際大宗商品價(jià)格下跌,物價(jià)露出通縮苗頭;部分行業(yè)技術(shù)簡(jiǎn)單引進(jìn)消化的空間開始減小,面臨向原創(chuàng)性技術(shù)創(chuàng)新轉(zhuǎn)變。
無論從宏觀、中觀還是微觀,可以廣泛地觀察到,中國(guó)此輪經(jīng)濟(jì)減速主要是結(jié)構(gòu)性和體制性。更為重要的是,市場(chǎng)本該結(jié)構(gòu)性出清,卻由于體制性障礙難以實(shí)現(xiàn),刺激多、改革少,舊增長(zhǎng)模式拒絕退出,隱性擔(dān)保泛濫導(dǎo)致資金錯(cuò)配,形成三大資金黑洞(即舊增長(zhǎng)模式的鐵三角:房地產(chǎn)、地方融資平臺(tái)和產(chǎn)能過剩重化工業(yè)),醞釀金融風(fēng)險(xiǎn)和隱性失業(yè)。
2、政策應(yīng)對(duì)應(yīng)主要是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而非需求側(cè)總量刺激
如果經(jīng)濟(jì)減速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增長(zhǎng)平臺(tái)和動(dòng)力結(jié)構(gòu)不變,應(yīng)通過反周期性寬松政策刺激經(jīng)濟(jì)回歸增長(zhǎng)中樞。比如,2004-2005年是周期性減速,廉價(jià)勞動(dòng)力成本優(yōu)勢(shì)使得中國(guó)勞動(dòng)密集型工業(yè)品行銷世界,居民快速的住行消費(fèi)升級(jí)帶動(dòng)大量住房和基建投資需求,因此政策適度放松后,2006-2007年經(jīng)濟(jì)重回周期性繁榮。
但是,如果經(jīng)濟(jì)減速是結(jié)構(gòu)性和體制性,增長(zhǎng)平臺(tái)和動(dòng)力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體制性因素阻礙了結(jié)構(gòu)性出清,固化了原有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產(chǎn)能過剩企業(yè)淪為“僵尸企業(yè)”,只刺激不改革實(shí)際上是延緩舊增長(zhǎng)模式出清和鼓勵(lì)加杠桿,是“明斯基時(shí)刻”并引向金融危機(jī)的節(jié)奏。
2008年國(guó)際金融危機(jī)以來,面臨經(jīng)濟(jì)下行,我國(guó)先后采取了以財(cái)政刺激、貨幣放水等為主的政策工具應(yīng)對(duì),但均未能有效解決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問題,并留下大量的風(fēng)險(xiǎn)和后遺癥,政策取向最終選擇以“供給側(cè)改革”為主。2009年我國(guó)采取了4萬億財(cái)政刺激,雖然在當(dāng)時(shí)應(yīng)對(duì)國(guó)際金融危機(jī)中起到了救急的作用,但也導(dǎo)致重化工業(yè)死灰復(fù)燃、產(chǎn)能過剩加劇、金融風(fēng)險(xiǎn)積累等后遺癥。2014年以來,我國(guó)采取了貨幣寬松,雖然在降低企業(yè)融資成本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導(dǎo)致股市一線房市等資產(chǎn)價(jià)格泡沫、延緩過剩產(chǎn)能出清等負(fù)面效果。
當(dāng)前中國(guó)經(jīng)濟(jì)表面上是增速換擋,實(shí)質(zhì)上是結(jié)構(gòu)升級(jí),根本上靠改革轉(zhuǎn)型。
2011年任澤平原來所在的國(guó)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團(tuán)隊(duì)在國(guó)內(nèi)最早提出了“增長(zhǎng)階段轉(zhuǎn)換”,后來中央采納為“增速換擋”。2014年任澤平加盟國(guó)泰君安證券[微博]以后,在資本市場(chǎng)上嘗試建立“轉(zhuǎn)型宏觀”框架來解釋和預(yù)測(cè)中國(guó)經(jīng)濟(jì)與資本市場(chǎng)未來,提出“新5%比舊8%好”(2014年7月19日),未來通過改革構(gòu)筑的5%新增長(zhǎng)平臺(tái),比過去靠刺激勉強(qiáng)維持的7%-8%舊增長(zhǎng)平臺(tái)要好,經(jīng)濟(jì)從要素驅(qū)動(dòng)型向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型轉(zhuǎn)變,增長(zhǎng)模式從速度效益型向質(zhì)量效益型升級(jí),產(chǎn)業(yè)從重化工業(yè)為主向高端制造業(yè)和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為主升級(jí),企業(yè)利潤(rùn)上升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邁向繁榮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新常態(tài)”。
二、資本市場(chǎng)在供給側(cè)改革中將承擔(dān)重要使命
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出路在于通過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改革,推動(dòng)重化工業(yè)領(lǐng)域過剩產(chǎn)能出清,放活高端制造業(yè)和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資本市場(chǎng)在“去產(chǎn)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bǔ)短板”的供給側(cè)改革中將承擔(dān)重要使命。
1、黨中央國(guó)務(wù)院十分重視發(fā)揮多層次資本市場(chǎng)在供給側(cè)改革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中的重要作用和使命
2015年12月18-21日中央經(jīng)濟(jì)工作會(huì)議提出“著力加強(qiáng)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并多次論述多層次資本市場(chǎng)在“去產(chǎn)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bǔ)短板”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盡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chǔ)制度扎實(shí)、市場(chǎng)監(jiān)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quán)益得到充分保護(hù)的股票市場(chǎng),抓緊研究提出金融監(jiān)管體制改革方案”、 “擴(kuò)大直接融資比重”“資本市場(chǎng)要配合企業(yè)兼并重組”“支持企業(yè)技術(shù)改造和設(shè)備更新,降低企業(yè)債務(wù)負(fù)擔(dān),創(chuàng)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業(yè)技術(shù)改造投資能力。”“加強(qiáng)全方位監(jiān)管,規(guī)范各類融資行為,抓緊開展金融風(fēng)險(xiǎn)專項(xiàng)整治,堅(jiān)決遏制非法集資蔓延勢(shì)頭,加強(qiáng)風(fēng)險(xiǎn)監(jiān)測(cè)預(yù)警,妥善處理風(fēng)險(xiǎn)案件,堅(jiān)決守住不發(fā)生系統(tǒng)性和區(qū)域性風(fēng)險(xiǎn)的底線。”
2015年12月23日國(guó)務(wù)院常務(wù)會(huì)議,“確定進(jìn)一步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措施,提升金融服務(wù)實(shí)體經(jīng)濟(jì)效率”。提出“加大金融體制改革力度,優(yōu)化金融結(jié)構(gòu),積極發(fā)展直接融資,有利于拓寬投融資渠道,降低社會(huì)融資成本和杠桿率,推進(jìn)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改革,支持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平穩(wěn)運(yùn)行。
會(huì)議確定,一是完善股票、債券等多層次資本市場(chǎng)。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微博]戰(zhàn)略新興板,支持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融資。完善相關(guān)法律規(guī)則,推動(dòng)特殊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類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在境內(nèi)上市。增加全國(guó)中小企業(yè)股份轉(zhuǎn)讓系統(tǒng)掛牌公司數(shù)量,研究推出向創(chuàng)業(yè)板轉(zhuǎn)板試點(diǎn)。規(guī)范發(fā)展區(qū)域性股權(quán)市場(chǎng)。
二是豐富直接融資工具。積極發(fā)展項(xiàng)目收益?zhèn)翱赊D(zhuǎn)換債券、永續(xù)票據(jù)等股債結(jié)合產(chǎn)品,推進(jìn)基礎(chǔ)設(shè)施資產(chǎn)證券化試點(diǎn),規(guī)范發(fā)展網(wǎng)絡(luò)借貸。簡(jiǎn)化境內(nèi)企業(yè)境外融資核準(zhǔn)。三是加強(qiáng)資信評(píng)級(jí)機(jī)構(gòu)和會(huì)計(jì)、律師事務(wù)所等中介機(jī)構(gòu)監(jiān)管,研究證券、基金、期貨經(jīng)營(yíng)機(jī)構(gòu)交叉持牌,穩(wěn)步推進(jìn)符合條件的金融機(jī)構(gòu)在風(fēng)險(xiǎn)隔離基礎(chǔ)上申請(qǐng)證券業(yè)務(wù)牌照。
四是促進(jìn)投融資均衡發(fā)展。逐步擴(kuò)大保險(xiǎn)保障資金在資本市場(chǎng)的投資,規(guī)范發(fā)展信托、銀行理財(cái)?shù)韧度谫Y功能,發(fā)展創(chuàng)投、天使投資等私募基金。五是強(qiáng)化監(jiān)管和風(fēng)險(xiǎn)防范,加強(qiáng)相關(guān)制度建設(shè),堅(jiān)決依法依規(guī)嚴(yán)厲打擊金融欺詐、非法集資等行為,切實(shí)保護(hù)投資者合法權(quán)益。”
2、未來隨著A股逐步調(diào)整到位、泡沫去化進(jìn)入尾聲,推動(dòng)資本市場(chǎng)改革迎來重要機(jī)遇和時(shí)間窗口
快牛快熊均不利于資本市場(chǎng)改革的推動(dòng),風(fēng)險(xiǎn)是漲出來的,機(jī)會(huì)是跌出來的。隨著A股逐步調(diào)整到位、泡沫去化進(jìn)入尾聲,市場(chǎng)正逐步進(jìn)入正常狀態(tài),估值趨于合理,投資者趨于理性,這為資本市場(chǎng)改革迎來重要機(jī)遇和時(shí)間窗口。
在推動(dòng)資本市場(chǎng)改革過程中應(yīng)注重理論現(xiàn)實(shí)相結(jié)合、部門協(xié)調(diào)、政策配合、對(duì)稱創(chuàng)新等。中國(guó)A股由于投資者結(jié)構(gòu)以散戶主導(dǎo)、法治尚待完善等原因,博弈氣氛較濃,價(jià)值投資理念有待傳播,呈典型的新興市場(chǎng)特點(diǎn),因此在市場(chǎng)化方向前提下,注冊(cè)制等重大改革要考慮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情況。
面對(duì)日益混業(yè)的金融發(fā)展趨勢(shì),各領(lǐng)域金融風(fēng)險(xiǎn)之間交叉?zhèn)魅荆乐贡O(jiān)管職能的碎片化,推動(dòng)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監(jiān)管機(jī)制的建立。財(cái)政、貨幣、匯率等政策對(duì)資本市場(chǎng)均產(chǎn)生重要影響,各部門各政策間應(yīng)做好配合,比如2014年11月21日第一次降息后A股大漲,應(yīng)加快推動(dòng)注冊(cè)制改革和股票供給增加;2015年1月4日前后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引發(fā)資金流出壓力,A股可提前明確1月8日大股東解禁新規(guī)、釋放利好予以對(duì)沖相關(guān)影響。
目前A股資金存量博弈環(huán)境下,推動(dòng)注冊(cè)制改革、戰(zhàn)略新興板等將引起股票供給增加擔(dān)憂,可以考慮同時(shí)推動(dòng)養(yǎng)老金入市等資金需求的承接。
3、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chǔ)制度扎實(shí)、市場(chǎng)監(jiān)管有效、投資者權(quán)益得到充分保護(hù)的股票市場(chǎng),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升級(jí)
未來要大力發(fā)展高端制造業(yè)、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和民營(yíng)中小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具有高知識(shí)、高技術(shù)、高風(fēng)險(xiǎn)、輕資產(chǎn)、缺乏抵押物等特點(diǎn),這與傳統(tǒng)銀行主導(dǎo)的金融體系不匹配,金融結(jié)構(gòu)落后對(du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升級(jí)構(gòu)成了制約。未來應(yīng)大力發(fā)展多層次資本市場(chǎng),支撐新興產(chǎn)業(yè)發(fā)展壯大。應(yīng)把推動(dòng)注冊(cè)制改革作為發(fā)展多層次資本市場(chǎng)的牛鼻子工程,實(shí)現(xiàn)市場(chǎng)定價(jià)、從事前監(jiān)管到注重事中事后監(jiān)管、法治公開透明等。
一步到位的、徹底的注冊(cè)制改革對(duì)法治環(huán)境、事中事后監(jiān)管、退市制度等要求較高,在相關(guān)法治保障不健全的情況下實(shí)行美國(guó)式注冊(cè)制將使資本市場(chǎng)淪為更為嚴(yán)重的圈錢游戲,這是完全可以預(yù)料到的。從老成謀國(guó)的角度,建議采取漸進(jìn)式的注冊(cè)制改革,往前走半步,先降低上市的盈利門檻、適度擴(kuò)容但仍有節(jié)奏控制、審核主體下放到交易所、交易所對(duì)注冊(cè)文件的齊備性一致性可理解性進(jìn)行審核,并逐步建立完善事中事后監(jiān)管、集體訴訟制度、欺詐重罰、退市制度等重大保障制度。
4、大力推進(jìn)資產(chǎn)證券化,化解金融風(fēng)險(xiǎn)
化解金融風(fēng)險(xiǎn)是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改革的一個(gè)關(guān)鍵點(diǎn)。大力推進(jìn)資產(chǎn)證券化,有利于盤活企業(yè)資產(chǎn),化解債務(wù)風(fēng)險(xiǎn)和流動(dòng)性風(fēng)險(xiǎn)。例如,ABS(信貸資產(chǎn)證券化)有利于盤活信貸資產(chǎn),提高銀行資產(chǎn)周轉(zhuǎn)率,化解銀行風(fēng)險(xiǎn);REITs(房地產(chǎn)信托投資基金)等有利于盤活房地產(chǎn)資產(chǎn),化解房地產(chǎn)企業(yè)風(fēng)險(xiǎn)。銀行和房地產(chǎn)相關(guān)風(fēng)險(xiǎn)是構(gòu)成我國(guó)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重要方面。
5、發(fā)展開放、包容的多層次資本市場(chǎng),降低企業(yè)融資成本
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chǎng),大力發(fā)展直接融資,降低權(quán)益融資門檻,創(chuàng)新債券融資工具等,對(duì)拓寬企業(yè)特別是中小企業(yè)融資渠道意義重大,有效降低中小企業(yè)融資成本。
6、鼓勵(lì)通過資本市場(chǎng)優(yōu)化重組,化解落后產(chǎn)能
充分發(fā)揮資本市場(chǎng)在企業(yè)優(yōu)化重組過程中的渠道作用,強(qiáng)化資本市場(chǎng)的產(chǎn)權(quán)定價(jià)和交易功能,拓寬并購融資渠道,豐富并購支付方式。尊重企業(yè)自主決策,鼓勵(lì)各類資本公平參與并購,破除市場(chǎng)壁壘和行業(yè)分割,實(shí)現(xiàn)公司產(chǎn)權(quán)和控制權(quán)跨地區(qū)、跨所有制順暢轉(zhuǎn)讓。構(gòu)建有效的股市退出機(jī)制、債券違約機(jī)制和打破剛兌機(jī)制,減少對(duì)落后企業(yè)的支持,有利于落后企業(yè)退出市場(chǎng)。
7、依托資本市場(chǎng),放寬準(zhǔn)入,引入新的投資者,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yè)改革
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領(lǐng)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y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lǐng)域,依托資本市場(chǎng),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lì)加強(qiáng)競(jìng)爭(zhēng),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8、實(shí)施結(jié)構(gòu)性減稅,鼓勵(lì)創(chuàng)新
經(jīng)濟(jì)衰退期應(yīng)通過減稅放水養(yǎng)魚,尤其是對(duì)于企業(yè)加大技術(shù)創(chuàng)新投入、加速折舊、VCPE等給與稅收優(yōu)惠。保護(hù)產(chǎn)權(quán),穩(wěn)定企業(yè)家預(yù)期,促進(jìn)創(chuàng)新要素流動(dòng),培育人力資本,構(gòu)建鼓勵(lì)創(chuàng)新的金融體系。
9、推動(dòng)國(guó)企改革,提高資產(chǎn)證券化率
資本市場(chǎng)將是支撐國(guó)企改革重要力量。推動(dòng)國(guó)企分類監(jiān)管,成立國(guó)有資本運(yùn)營(yíng)公司,試點(diǎn)股權(quán)激勵(lì)和員工持股,實(shí)現(xiàn)國(guó)企資產(chǎn)證券化和混合所有制深度嵌合。
10、在推動(dòng)供給側(cè)改革的同時(shí),建設(shè)社會(huì)“完全網(wǎng)”,兜住社會(huì)穩(wěn)定的底線
供給側(cè)改革將會(huì)對(duì)銀行不良、P2P、就業(yè)等產(chǎn)生沖擊,化解之策在于債務(wù)重組剝離、大力發(fā)展服務(wù)業(yè)、完善社會(huì)保障體系、完善失業(yè)救濟(jì)等。
三、隨著供給側(cè)改革破冰攻堅(jiān),各界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前景將更有信心
隨著供給側(cè)改革破冰攻堅(jiān),各界對(duì)中國(guó)此輪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的未來將更有信心,中國(guó)不會(huì)落入拉美中等收入陷阱,中國(guó)有龐大的實(shí)體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充裕的人力資本紅利、富有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活力的企業(yè)家隊(duì)伍,這跟以資源為主的拉美國(guó)家有根本不同,更類似成功實(shí)現(xiàn)增速換擋和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日本與韓國(guó)。
我們處在30年未有之變局的轉(zhuǎn)型時(shí)代,處在一個(gè)偉大的變革時(shí)代,一輪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的變革正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開,這為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提供了廣闊的舞臺(tái)。我們深信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理念已經(jīng)在這個(gè)國(guó)家扎根,新一屆中央領(lǐng)導(dǎo)集體展現(xiàn)了推動(dòng)改革的勇氣和決心。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改革是唯一的出路。道路雖然曲折,過程雖然伴有陣痛,但經(jīng)歷過改革轉(zhuǎn)型之后的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前景將更加光明。
(本文作者介紹:國(guó)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jīng)理、首席宏觀分析師,中國(guó)金融40人論壇特邀研究員、中國(guó)新供給50人論壇成員、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兼職研究員等。曾擔(dān)任國(guó)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


 手機(jī)資訊
手機(jī)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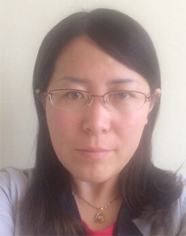



 豫公網(wǎng)安備41019702003646號(hào)
豫公網(wǎng)安備41019702003646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