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材料面臨的困境,第一條就是‘等米下鍋’。”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邱勇直言不諱,新材料從研發到成熟應用往往需要漫長過程,而目前我國的新材料發展大大滯后于制造業的需求。
12月20日,在南京舉行的2018中國新材料產業發展大會上,30余位院士以及近3000材料業內人士到會,材料創新與產業化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產業升級,材料先行。材料是國家制造業的基礎,新材料研發水平及產業化規模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經濟實力的重要標志,在發展高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防實力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新材料產業起步晚、底子薄,整體實力還比較薄弱。
“我國的新材料產業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中科院院士魏炳波說,2017年我國新材料產業規模達3.1萬億元,但是創新能力和競爭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較大差距。相關部委對130多種關鍵材料的調研顯示,有32%還處于空白,52%依賴進口;95%的高端專用芯片、70%以上智能終端處理器及極大多數存儲芯片依賴進口;國外對我國實施的“卡脖子”項目中,一多半屬于新材料領域。
先進的技術買不來。江蘇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劉慶教授作為一名金屬材料專家深有體會:“我國許多材料的制造裝備是世界最先進的,但是卻生產不出最先進的材料。”他告訴記者,全國領先的工程機械行業龍頭企業徐工集團,其制造高噸位起重裝備的伸縮臂筒用鋼板仍然需要進口;南高齒的高強齒輪鋼至今仍需進口;我國目前在研的大飛機、發動機、艦船等都面臨核心部件急需突破材料及其制備工藝問題。
“如果沒有怎么辦,先用別人的,自己再追趕。但是這種備受國內產業界推崇的后發優勢,在很多材料領域并不存在。”邱勇說,新材料產業恰恰相反,存在“后來者劣勢”,即不容易被市場接受。初期市場培育,是新材料推廣應用的關鍵環節,新材料“首批次”推廣應用困難,是制約我國新材料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的關鍵瓶頸。
與會專家指出,目前我國的新材料產業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不夠,存在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原始創新能力不足,共性技術研發與支撐能力不強,高端產品自給率不高;新材料投資分散,產業鏈不夠完整,作為發展主體的新材料企業普遍規模較小,轉化率低;政策及保障機制難以適應新材料產業發展的要求,存在“老辦法管新事物”的現象。
如何構建一個研發能力強、產業融合度高的新材料創新體系也被提上議事日程。“新材料發展應該是創新與應用并重。”邱勇認為,材料技術具有長鏈條、跨尺度等特點,新材料從研發到成熟應用往往需要漫長過程,材料不在應用中不斷完善性能,工藝技術就無法迭代優化,一些關鍵的數據也無法積累。
但是,在我國已有的材料研發機構中,大學的相關研究偏重自由探索,缺乏系統性;科學院研究所注重學科導向,與產業結合不夠;行業企業研究機構注重技術的快速提升,原創性缺乏,都難以滿足我國制造業和材料產業多年來高速發展對新材料科技的需求。
目前,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在材料領域依托國家級研發平臺已建立了6家研究所,與地方政府和創新團隊共同建立了8家研究所,涵蓋了先進金屬材料、高溫合金材料、碳纖維及復合材料、膜材料、功能性纖維材料等領域。
“要加強原創性研究,加速新材料及其制備、生產技術的研發,必須啟動新的機制體制探索。”劉慶說,鑒于我國新材料產業的迫切需求,江蘇省產研院將整合其材料板塊已有的資源,聯合協調材料領域龍頭企業、高校、科研院所,規劃成立江蘇先進材料技術創新中心。
據介紹,該中心最大的特點是機制靈活、開放共享,以材料產業前沿引領技術和關鍵共性技術研發與應用為核心,加強應用基礎研究,加大重大關鍵技術源頭供給,不與高校爭學術之名,不與企業爭產品之利。通過三年左右第一期建設,攻克高強高模碳纖維、第五代單晶高溫合金、新型儲氫材料等一批新材料產業前沿和共性關鍵技術;在先進金屬材料、碳纖維及其復合材料、膜材料、高分子材料等領域初步形成發展潛力大、帶動作用強的創新型產業集群。


 手機資訊
手機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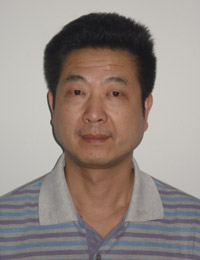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46號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46號